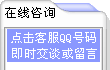死亡之妆 |
| 责任编辑:也仪
日期:2005/11/3 20:45:20 浏览:1028次
文字大小[大 中 小] |
(1)--停尸房里的男尸
像很多恐怖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发生在医院,一所座落在市郊的医院。医院四周有山有水,树木郁郁葱葱,到了晚上,风一刮起来,那些树木哗哗啦啦作响,有几分阴森。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地形:
进了这个医院的大门,先是门诊楼,然后是住院部,最后是停尸房。停尸房位于医院
大院的最后边,从住院部到停尸房,是一片空地。一条曲折的石径小道,四周生满了荒草。
不要怀疑你自己的抗恐怖心理素质,其实我们都一样,对停尸房这类地方都胆战心惊,不愿意接近它。这可以理解为活人对死人的恐惧,也可以理解为生命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停尸房的四周就空空荡荡。因此,这里的风就很大。因此,它就显得更恐怖。
这家医院很小,前来看病的人不多,停尸房也长年空着。里面,很潮很暗,有一股霉味。没有专人看管。只有一扇黑洞洞的小窗,像一个简陋的子宫,回收报废的生命。
有一天,停尸房放进一具男尸,是个老头,死于癌。他很老了,脸上的皱纹像深刻的蜘蛛网。据说,他生前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见了猫都害怕,自从他变成一具尸体,人们立即对他充满恐惧了。
怕什么呢?他已经定了格,变成了一张照片。大家可能是怕那张照片突然笑起来。
这具尸体只在停尸房放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他的家人要把他送到火葬场去,可是却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老头果然笑起来。
他苍青的脸扑了厚厚的粉,眉毛也画了,弯弯的女人眉,还戴了长长的假睫毛。毫无血色的嘴唇竟然涂了很红很红的口红,嘴角向上翘,一副微笑的模样。
他的家人第一眼吓坏了。惊慌地退到门口,看了半天,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马上愤怒地质问医院负责人,负责人当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医院决定查一查。
那天晚上,有一个值班男医生和一个值班女护士。男医生叫黄玉凤,性格很孤僻,不爱与人交流,没有人了解他。他头发很长,戴一副黑框眼镜,眼睛后面总像还有一双眼睛。他上班下班总是不脱他的白大褂。
他已经下班回家了,医院领导首先把他叫来。
院长:“黄大夫,昨夜你值班,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啊?”
他看着院长的眼睛,平静地说:“没有。”
院长没有避开他的眼光,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表情,突然问:“你最近是不是总失眠?”
黄玉凤说:“没有。”
院长问:“夜里有没有出去转一转?”
院长的话音还没有落,他就冷静地否认了:“没有。”还是看着院长的眼睛。
院长笑了笑:“那你干什么了?”
他淡淡地说:“看一部小说,推理的。”
院长问:“你几点睡的?”
黄玉凤医生:“我没睡。”
院长:“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有失眠吗?”
黄玉凤医生:“我夜里很少睡觉。”
院长:“那没听到一点动静?”
黄玉凤医生说:“很多猫一直叫。”
院长终于躲开他的眼神,点着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昨天我们医院发生了一点事情,你知道吗?”
黄玉凤一点都不惊诧,他一直看着院长的眼睛,说:“不知道。”
院长:“也没有多大的事。好吧,你去吧。”
接着,院长又叫来那个值班女护士。她叫葛桐,正在热火朝天地谈恋爱,是个很外向的女孩子,快言快语,平时大家都喜欢她,把她当成单调工作中的调味剂。
听了事件的经过,葛桐吓得脸都白了。
院长问她昨夜有没有听见黄玉凤医生出门。她努力回忆昨夜的每一个细节:“我查了各个病房,然后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再然后……就睡了,一觉睡到天亮,什么也没有听到呀。”
她请求院长:“领导,您饶了我吧,今后别安排我值夜班了,我这个人天生胆子就小,天黑都不敢看窗外。”
院长说:“那怎么行呢?每个职工都要值夜班,这是制度。”
葛桐是个说话不绕弯的女孩子,她脆快地说:“院长,要不然您把我的班串一串。黄医生怪怪的,我怕他。”
院长说:“他就是那种性格,其实没什么。”
然后,他开导了葛桐一番,最后,葛桐撅着嘴走了。
查不出结果,院长只好作罢。
他分明地感觉出,如果是医院内部的人所干的事,那么百分之九十是黄玉凤医生所为。只是他拿不出直接的证据。
从此,医院里的人对黄玉凤医生有了戒备。大家都在谈论这个死尸化妆的怪事,但没有人和黄玉凤医生谈论此事。
黄玉凤医生和从前一样,见了谁都不说话。和病人说话也是很简单,简单得有时候话语都残缺不全。没有事的时候,他就拿一本推理书阅读。不烟不酒,不喜不怒,他是个没有特征的人,是个没有表情的人。
2)--惊恐之旅
时光踏着日月沉浮的节奏,缓缓地前行。撕心裂肺的爱情,不共戴天的仇恨,都可以被时光的力量吞噬。同样,大家心中那恐怖的阴影也一点点淡化了。那个莫名其妙的事件经过很多的嘴,最后变得更加神乎其神,其中有一个细节已经成立,那就是尸体确实是笑了。同时,它在医院后来的工作人员眼里,也一点点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可信度的传说。
因此我们最好不要一概否定一些传说的母本的真实性。有一句老掉牙的话:无风不起
浪。
葛桐这个人不会表演,她作为那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每次见了黄玉凤医生,都无法掩饰住对他的猜疑和害怕,所以后来她再和他相遇,总是远远就躲开。
有一个周末,葛桐下了班准备去城里。城里离医院大约有60里。长途车在这个镇郊医院围墙外有一站。吃过饭,她背着包要出发了。天快黑了,葛桐快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远远看见了黄玉凤医生,她穿着白大褂,莫名其妙坐在大门口,不知道干什么,好像就是为了堵截她一样。他和葛桐这一天都不值班,周末除了值班的人都应该回家了。葛桐不敢从大门口走出去,她只好绕路走,翻墙出去了。
她一路小跑来到公共车站牌前,正好上车,她气喘吁吁地在一个空位上坐定,一抬头,差点惊叫出来:穿着白大褂的黄玉凤医生脸色苍白地坐在她旁边,正看着她!
葛桐惊恐地看着黄玉凤医生,半晌才说:“黄大夫,刚才我怎么看见你坐在医院的大门口……”
“不是我。”他冷冷地打断她。
葛桐说:“那可能是我看错了。”天要黑了。
通往城里的公路空荡荡。
黄玉凤医生也去城里。巧合?
“呀,我忘了一件事……”葛桐说。
黄玉凤医生毫无表情地看着她。
“我有一件衣服晾在药房外面了。”她说得结结巴巴,任何人都能看出她在撒谎。“我应该回去……”
就在这时候车开动了。
“咳,算了。”她又不自然地说。
车走着。没有售票员,只有一个司机。
两个人都不说话。
车上的人不多,都不说话。那种静默就像印象派电影。
天快黑了。
车偶尔经过一座村庄,节俭的人们还没有点灯,村庄暗淡。路边是北方常见的白杨树,高大,挺拔,胸怀坦荡。
车上柴油味刺鼻。
葛桐有点恶心,心情更糟糕。
她先开口了:“黄大夫,你去城里干什么呀?”
“没什么具体事。”
葛桐:“我去我哥哥家。”
黄玉凤医生敏感地转过头看着葛桐:“他接你吗?”
葛桐:“是的,电话里说好了。”她说这句话又结巴了。
黄渔凤医生不再接她的话头。
天快黑了。
车慢吞吞地停下来,到了第一站,是公路的一个大十字口。乘客陆续下车,竟然都下光了,只剩下葛桐和黄玉凤医生。
最后一个人下车的时候,葛桐的神色更加慌乱了。
车“哐当”一声关了门,又慢吞吞地朝前走。
其它的座位都空着,葛桐和黄玉凤医生坐在一起,他们在慢节奏对着话。
葛桐不看黄玉凤医生的脸,她大声问:“黄医生,你是哪里人?”
黄玉凤医生:“外省人。”
葛桐:“很远吧?”
黄玉凤医生:“关里。”
葛桐:“怎么来这个小镇了?”
黄玉凤医生:“命。”
葛桐:“你今年不到三十岁吧?”
黄玉凤医生:“四十多了。”
葛桐:“这正是男人干事业的年龄。”
黄玉凤医生:“我最大的愿望可不是医疗。”
葛桐转头看了看黄玉凤医生:“那是……”
黄玉凤医生叹口气:“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他很瘦,干巴巴的身子裹在白大褂里显得很可怜。他为什么总是不脱白大褂?他呈现给人的永远是这一种表情,这一种装束,好像是一张照片,一张医生的工作照。
葛桐一直在问,好像要尽可能地接近这个古怪的人。可是他那无神的眼睛却让人捕捉不到任何信息。
停了停,葛桐:“你太太也是外省人吗?”
黄玉凤医生:“是。”
葛桐沉默半晌:“你们有孩子吗?”
黄玉凤医生:“没有。”
葛桐:“为什么还不要孩子?”
黄玉凤医生:“我们早离婚了。”
葛桐:“你一个人生活?”
黄玉凤医生:“还有一只猫。”说到这里他奇怪地笑起来。
葛桐显得很不自在:“你太太是干什么的?”
黄玉凤医生想了想,慢吞吞地说:“美容。”
葛桐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她慢慢转过头,看着正前方。
天快黑了,看什么都有点看不清楚了。
又经过村庄,村庄的灯亮起来。
路还远。
黑暗是一种压力,铺天盖地缓缓降落。车灯亮了,前途惨白。葛桐盼望那个司机偶尔回一下头,却不能如愿。她上车后再也没有看见那个司机的脸,只是一个背影。
车颠簸起来。
黄玉凤医生纹丝不动。
葛桐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突然问:“黄医生,你喜欢美容吗?”
黄玉凤医生平静地说:“不喜欢。”
说完,他双眼闪亮地看着葛桐:“你怎么问这个?”
葛桐惊慌失措地低下头:“我随便问问。”
葛桐问完这句话,黄玉凤就靠在椅子背上,慢慢闭上双眼,似乎不想再说话。
整个车厢彻底静默,气氛沉重。
葛桐没有睡,她一直警惕地睁着眼睛,她的余光严密地关注着身边的黄玉凤医生。他没有一点声息,似乎睡得很香。
终于进城了,是一条很偏的街道,路灯昏黄,没有行人。
车还在朝前走。
假如闭上眼睛,没有任何声音提示现在已经进了城。
可是,就在这时候,黄玉凤医生冷静地睁开眼睛,抻了抻白大褂的领子,准备下车了——看来他对一切了如指掌。
车停了。
葛桐坐的位置靠车门,她指着车外面一个陌生男子说:“黄医生,我下车了,我哥哥在那里。”
黄玉凤医生抬头看了看,平静地说:“他不是。”
葛桐顿时又惊诧又尴尬,她掩饰说:“我这眼睛怎么了,总出错!我走啦,黄医生,再见。”
“再见。”
葛桐和黄玉凤医生告了别,大步朝前走。走了十几米,她紧张地回头看了看,根本没有黄玉凤医生的影子。
(3)--没有胆大的人
有一次,轮到黄玉凤医生和葛桐值班的时候,停尸房又放进了一具尸体。
葛桐又找院长了,请求换班。她哭起来,如果院长不为她换班,她就要辞职了。
为了照顾小姑娘葛桐,院长决定再派一个男医生和黄玉凤医生一起值夜班。院长是个很有威力的院长,他虽然没什么文化,是个大老粗,工作作风更像一个村支书,但是他什么
事都身先士卒,雷厉风行,大家都挺敬畏他,平时他说什么没有人不服从。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快下班的时候,院长叫来外科的田大夫,对他说:“你今夜和黄玉凤医生一起值夜班,串一串。”并没有多说什么。
田大夫立即苦着脸说:“院长啊,我家的小孩高烧,正在家昏睡着,我老婆白天都想让我请假呢!”院长知道,平时田大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孩子发高烧,他今天肯定不会来上班。而且,院长今天见他很喜兴,中午休息还打了一个半小时的牌,他那独子是他命根子,如果有病,他不会如此轻松,中午早骑车回家看望了。家属楼离医院只有十分钟的路。但是他把孩子拿出来当盾牌,院长又不好说什么,否则就太不近人情了。
院长沉吟片刻,说:“那好吧,你帮我叫一下李大夫。”
不一会,内科的李大夫来了。
院长说完值夜班的事,问:“你今晚有没有什么事情?”
李大夫说:“没什么,只是今天是我和老婆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当然要和老婆好好过一下。晚上老婆还在酒店定了几桌席,要宴请一些亲戚和朋友,闹一闹,图个喜庆呗,所以……”
李大夫这个理由更让院长无话可说。人家这是第二个婚礼,第二个洞房花烛夜,你让人家值班?其实院长心里明白,李大夫爱张扬的男人,如果他说的是真话,他早就四处奔走相告了。连他小孩当了三好学生这样一件事,他在一天内就传遍了整个医院。上次他爸爸过五十九大寿,他一上班就各个办公室广而告之了,害得大家每个人都送去一张钞票做贺礼。如果今天真的是他和他老婆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他这一天能不说?至少要请院长到场吧?
院长说:“算了,你帮我叫一下秦大夫。”
妇科的秦大夫还是个小伙子,刚刚毕业,在医院里年龄最小,上次发生那件怪事的时候他还没有来。院长想他不会遍什么谎话。一进门,院长就说:“秦大夫,你今夜和黄大夫值班,没问题吧?”
秦大夫马上一脸惊慌,眼睛转了转,央求说:“院长,求求您,换别人吧,我胆小。”
院长有点生气了:“你有什么可怕的!”
秦大夫说:“您让我打扫一年厕所都行,我就是不敢和他值夜班。求求您派别人吧……”
院长大声说:“你刚来就不服从领导,我处分你!”
秦大夫的神情很难过,他说:“院长,您处分我……我也不敢!”
院长想了想,说:“听说黄大夫原来的老婆是搞美容的,你帮我打听一下关于她的情况,这总可以吧?”
“好,没问题!”秦大夫立即满口答应。
“你去吧。”
“谢谢,谢谢院长!”秦大夫好像怕院长反悔似的,机敏地溜掉了。
最后,院长让葛桐和黄玉凤医生都回家了,他把自己和另外一个老护士留下来值班。
那天院长亲眼看见黄玉凤穿着白大褂离开了医院。夜里,院长来到住院部和停尸
房之间的那片空地转了转。他竟然看见停尸房的方向有一个白色的影子,在黑暗中一闪就消失了。很像黄玉凤医生。他追过去,没有任何人,只有掉在草地上的一本书,被风刮得“哗啦哗啦”响。那是一本多年前的推理书,作者是日本的,叫什么横沟正史。
院长突然有点恶心。
(4)--那个消失多年的美容女人
这一夜,没有人让那个死尸笑,于是他就没有笑。
之后的几天,院长一直在追问关于黄玉凤医生前妻的情况,秦大夫总是无奈地对院长说:多年前,黄大夫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没有人听说他结过婚,更没有人知道他有什么搞美容的前妻。
院长说:“这是他自己说的,没错。”
秦大夫:“他对谁说的?”
院长:“葛桐。”
秦大夫:“也许他是在编造谎言。”
院长:“编造这样的谎言有什么用?”
秦大夫:“他怪怪的,谁能摸清他想什么!或许是幻想狂。”
院长:“你还要打听,不能放弃。因为弄清楚这个搞美容的女人,很可能对我们调查前一段时间那件奇怪的事至关重要。”
秦大夫:“调查那件事有什么意义啊?”
院长:“出这样奇怪的事,严重影响了我们医院的形象。这是我们管理上的漏洞。我们要尊重患者,包括死去的患者,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又过了一段时间,秦大夫到市医院办事,回来,他兴冲冲地跑到院长的办公室来,他一进门就说:“院长,有消息了!”
市医院碰巧有一个热心的医生,他和黄玉凤医生是大学同学。秦大夫和他聊起来。那个热心的医生说,那个年代黄玉凤医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独来独往,从来不与人交流,同学们对他内心的了解,比现在你们医院里的同事多不了多少。但是他知道,黄玉凤医生原来在关里工作,结过婚,又离了。关于那个女人,他只知道她是一个美容师,出奇的漂亮。除此再不知道其它了。
当天,那个医生又给另一个更熟悉情况的老同学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又了解到了一点情况:
那个女人的美容手法极其高超,在当地小有名气,社交活动很多。有一次,她在云南开一个美容座谈会,认识了一个东南亚的一个老板,那个人在全世界有很多美容连锁店,很富贵,不久她就跟他远走高飞了。她走了之后杳无音信。很多年过去,她突然回来了,虽然衣着华丽,只是被人毁容了,那张脸特别吓人。她见了黄玉凤医生泪流满面。她和他相拥而眠,只过了一夜,第二天就投河了。
和许多类似的故事一样,那个老板有老婆,有几个老婆,也有情人,有很多情人。黄玉凤医生的老婆跟他到了东南亚,并不甘心情人之一的地位,她自不量力,不知深浅,跟那个老板闹事,跟他老婆争夺,终于被他老婆毁了容,用刀一下一下割的。他老婆的娘家势力更大,开的是挂皇家牌的轿车。黄玉凤医生的老婆远在异国,无依无靠,连个公道都讨不回来,最后就走投无路,就想到一死了之。可是她在离开人世之前只想看看曾经和他同床共枕的丈夫一眼……
说完,秦大夫说:“我想他是受了刺激。”
院长陷入怔忡。
(5)--那个日子又来了
巧的是,又一次轮到黄玉凤医生和葛桐值夜班的这一天,停尸房又放进了一具男尸,他被人用刀刺进腹中,抢救无效,死了。
整个医院骤然紧张起来,人心惶惶。
这天,院长打电话叫来了三个男大夫。
他们走进院长的办公室之前,还在小声谈论今夜,谈论那具死尸,谈论黄玉凤医生。他们根本没想到他们将面临一个大问题。
有时候,厄运就跟你隔一个墙角,你就茫然不知,你转身就撞在它的鼻子上。
他们刚刚坐定,院长就慢悠悠地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谁和黄大夫一起值班?”
三个男大夫立即傻眼了。接着,他们的脸色都变得苦巴巴了,支支吾吾要推脱。
还没等他们找理由,院长就说:“别编了,今天你们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
院长继续说:“你们抓阄。”
大老粗院长很快写了三个纸条。
三个男大夫没办法,犹犹豫豫地伸出手,抓凶吉。
一个姓张的大夫打开纸条,脸色暗淡下来。
一个幸运的男大夫得意地说:“张大夫,咱们三个人中你工资最高,你早应该主动把这个差事担下来!”
另一个男大夫也开玩笑:“其实没什么,不就是让老婆休息一下吗?”
张大夫叫张宇。他没有心情说什么,他一直脸色暗淡地坐在沙发上抽烟。
院长对另两个男大夫说:“你们先走吧,我和张大夫说几句话。”
他们离开之后,院长低声叮嘱张宇医生:“今夜你要严密关注黄玉凤医生的动向,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惊慌。”
张宇医生点点头,问了一句:“院长,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可以当武器的东西?”
这时候,开了一半的门口突然闪出黄玉凤医生的脸,很白。
他离院长和张宇医生很近,他应该很清楚地听见两个人说的话。只是不知道他来多久了。
院长没有看到黄玉凤医生,他说:“什么武器,别大惊小怪!”
张宇医生愣愣地看着黄玉凤医生的那张脸。
那张脸一闪,离开了。
张宇医生好半天没有回过神。
院长说:“记住,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惊慌!”
(6)--与怪人同室而寝
过去,吃过晚饭,医院里有些职工还常常来医院溜达溜达,聚一聚,聊一聊,打打牌,下下棋。自从出了上次那件事之后,大家都不到医院来了,躲都躲不及。下班后,医院里显得一天比一天冷清起来。
吃过晚饭,张宇医生来到门诊部各个房间巡视了一番。
他极其不愿意走进住院部二楼的那个值班室。
住院部这几天没有一个病人。
今夜又到黄玉凤医生动手的时候了。
想到这些张宇医生有些毛骨悚然。
天黑下来。
张宇医生终于慢慢地走向住院部,爬上二楼,走向值班室。
二楼的楼道很长,灯都坏了,黑漆漆的。
护士值班室在楼道顶头的那个房间,没有亮灯。葛桐一定很害怕,睡下了。
而医生值班室有灯光,但里边没有一点声音。
张宇医生在值班室门外站立,没有勇气走进去。
他甚至想一直在门外站下去,甚至想马上就给院长打电话,甚至想回家。
想归想,他最后还是推门进去了。
黄玉凤医生竟然不在。
张宇医生心里的石头放下了,又提起来。他脱掉衣裤,准备躺下。他想关掉房间灯,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关。他亮着灯钻进了被窝。
窗外的风大起来,吹得窗户“啪啪”地响。山上像是有什么野动物在叫,叫声遥远而模糊。
张宇医生的心跳得厉害。他在等着黄玉凤医生到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楼道里想起了脚步声,很大的脚步声,有点慢,但是他向值班室走来。
门“吱”地一声开了,张宇医生情不自禁地缩了一下脑袋。
进来的正是黄玉凤医生。
他认真地看了看躺在床上的张宇医生。张宇医生不自然地朝他笑了一下,算是打招呼。他也干巴巴地笑了一下。
然后,黄玉凤医生“咔哒”把房间的灯关了,他走到他床边,把床头灯打开。他慢慢脱掉衣服,穿着毛衣半靠在床上看书。
那床头灯很暗淡,一束光照在他的脸上,显得更加苍白。他慢悠悠地翻着书页,除此很静很静,听不到他的呼吸声。
张宇医生心里很压抑,他想找个话题,和黄玉凤医生聊一聊什么。但一时又想不起说什么。
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走得很小心,生怕一下撞到某一时刻上。
黄玉凤医生的书一页一页地翻。时间似乎停止了流动。
突然一阵巨响!张宇医生吓得差一点惊叫出来。
黄玉凤医生一动没动,眼皮都没眨一下,继续翻他的那本书。
是敲门声。
“谁?!”张宇医生问,声调都变了。
“是我!”是葛桐跑来了。
张宇医生披衣下地开门,他看见葛桐瑟瑟地抖,不知是冷的,还是吓的。
她看着张宇医生,欲言又止。张宇医生走出来,反手把门关上。
“张医生,我害怕……”她终于小声说。
张宇医生回头从门缝往里看了看,也小声说:“我不是在这里吗?不用怕。有什么事的话你喊一声我就过去了。”
“我不敢……”葛桐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了。
张宇医生硬撑着安慰她:“你都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而且是这里的值班人员,不能这样怯懦。不会有事的,天很快就亮了。”
葛桐无助地看看张宇医生,最后,只好裹紧睡衣,一步三回头地回去了。
张宇医生进屋,关好门,躺下来。他有了一种被人依靠的感觉,胆子略微壮了些。他轻轻地说:“黄医生,你平时很爱看书吗?”
黄玉凤医生淡淡地说:“夜里看。”
“你经常看谁的作品?”
“横沟正史的。”
张宇医生想说一点光明的事情,就问:“爱不爱看杂志?”
黄玉凤仍然淡淡地说:“我看我父亲死前留下的旧书。他的旧书有几箱子,看也看不完。”
风更大起来。门被穿堂风鼓动响了一下。
别人说“生前”,他偏要说“死前”——张宇医生的心缩紧了。
墙上的钟敲了十二下。
张宇医生怕到了极点。
他突然恼怒了,觉得这个怪兮兮的人要把自己弄崩溃!他索性豁出去了,用尽生命里全部的勇气,猛地坐起身子,直接刺向那个最敏感的话题:“黄医生,你说……那个男尸到底是被谁涂的口红呢?”
黄玉凤医生的态度令张宇医生无比意外,头都没有抬起来,冷淡地说:“也许是那个男尸自己。”
张宇医生没话了。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慢慢缩下身子,把头裹进被角,一动不动了。
黄玉凤的回答是一个高潮。他为这个故事说出了一个非常利落的结尾。可是,现实不是文学故事,任何人都无法设计结尾,现实还得继续。
张宇医生的心里更加惊惧。
墙上的钟走得更慢,“滴答滴答滴答”。
张宇医生再没有说话,他假装睡着了。
书一页一页地翻着,很响。
张宇医生咬着牙下决心,明天就跟院长说,下次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干这件事了。
过了很久,黄玉凤医生仍然在翻书。他不像是在阅读,而是在书中寻找一个永远找不到的书签。
(7)--他在看什么?
终于,黄玉凤医生把床头灯关掉了。房间里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张宇医生严密地聆听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像一直保持着那个倚在床头的姿势,没有脱毛衣钻进被窝。张宇医生感觉他正在黑暗中木木地看着自己。张宇医生吓得连气都不敢喘了。
又过了很久,张宇医生听见黄玉凤医生好像轻轻轻轻地下了床,在找鞋。他的声音太小了,张宇医生甚至不敢判定是那声音是否真实,他怀疑是自己的错觉。他的拳头攥紧了。
一个黑影终于从他面前飘过去,轻轻拉开门,走了。
张宇医生想跟出去,但是心里极其害怕。不过他很快又觉得一个人留在这个房子里等他回来更害怕!他最后披上外衣,轻轻从门缝探出脑袋,窥视黄玉凤医生到底要干什么。
黄玉凤医生在狭窄的楼道里蹑手蹑脚地来到葛桐的窗外,从窗帘缝向里偷看。也许是葛桐不敢睡觉,她房子里的灯微微的亮着。那条缝里流出的光照在黄玉凤医生的脸上,有几分狰狞。他表情阴冷地看了一会儿,又蹑手蹑脚地回来了。
张宇医生大惊,急忙钻回被窝里。黄玉凤医生进门,上床。这一次他脱了毛衣,进了被窝。
他去看什么?他看见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张宇医生假装起夜,披衣出门,也来到葛桐的窗前。
他朝里一看,头发都竖起来了!
葛桐坐在床边,神态怪异,双眼无神,她对着镜子,朝嘴上涂口红,涂得很厚很厚,像那具男尸的嘴一模一样。
她描眉画眼之后,直直地站起来,木偶一样朝外走出来。张宇医生急忙躲进对门的卫生间,听着葛桐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走远,他才闪身出来,心“怦怦怦”地跳着,鬼使神差地尾随她的背影而去。
葛桐走过黑暗的楼梯,走出楼门,右拐,在黑夜中朝楼后的停尸房方向走去。
张宇医生远远地跟着她。住院部大楼和停尸房之间的空地上,风更大。他看着她飘然一闪进了停尸房。张宇医生蹲下来,再也不敢靠近一步了。过了一会儿,他看见葛桐背着那具男尸走出来,踉踉跄跄地朝住院部走去。
张宇医生跟她进了楼,看着她背着男尸上楼梯。
她的身体有些单薄,竟然把那具男尸一直背上二楼,背进护士值班室,放在床上,然后在幽暗的灯光下一边为他涂口红,一边嘟嘟囔囔地对他说着什么。化妆完毕,她又背起男尸,出门,下楼……
大约十几分钟后,她像木偶一样走回来,洗脸,刷牙,上床,关灯,睡觉。
张宇医生傻了。他忽然明白了另一个道理:直觉、判断、推理、规律大多时候是南辕北辙的。在我们对我们的智慧、技术自以为是的时候,其实离真相、真理还差十万八千里。
张宇医生回到他的值班室,黄玉凤医生的床头灯亮了,他又在一页一页地翻书。
他淡淡地说:“张医生,你去厕所的时间真长啊。”
张宇医生惊恐地说:“是她!是她……”
黄玉凤医生没什么反应,冷冷地说:“夜还长呢,睡吧。”
次早,发现那具男尸的脸浓妆艳抹,整个医院又骚动起来。
院长一上班就知道了这个情况,他带两个值班男医生和葛桐一起去停尸房查看。葛桐看了那具男尸的样子,吓得惊叫出声来,接着就呕吐不止。
张宇医生轻蔑地说:“葛桐,别表演了,我昨天亲眼看见你把这具男尸背回来,为他化妆,又把他送回了停尸房!”
院长睁大了嘴巴。黄玉凤医生面无表情。
葛桐的脸色纸白,颤颤地指着张宇医生说:“张大夫,你血口喷人!肯定是你干的,却来诬陷我!”然后她极度委屈地哭起来。
张宇医生有点动摇。看表情,好像真不是她干的。难道自己是做梦?
他现在已经不信任一切了,包括自己的眼睛。他瞪着一双也许是出了错的眼睛直直地看葛桐,用他那一颗很可能是错上加错的大脑使劲地想。
院长看着葛桐的表情,又看着张宇医生的表情,迷糊了。是张宇医生干的?不可能啊。是葛桐干的?越想越离奇……院长想先稳住大家,就说:“这件事情很奇怪,但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找人把男尸的脸洗净就完了。大家回去吧。”
(8)--找朋友
院长非要大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半年后,黄玉凤医生和葛桐值班的时候,院长叫来两个院工,让他们假造一个尸体,然后放进停尸房。
晚上,他埋伏在医院里没有回家。他藏身在汽车里,汽车停在住院部和停尸房之间的
空地上。大约凌晨两点钟,他看见一个人木偶一样从楼角闪出,向停尸房走去。
院长也倒吸一口凉气,他壮着胆走出车门,径直朝那个人影追去。
正是她。她的脸涂了厚厚的粉,很白,在月光下有几分瘮人。
院长的腿也抖起来。他的社会职务是院长,他似乎不应该害怕。可他的人性与我们毫无二致。他哆哆嗦嗦地喊了一句:“葛桐,你去哪儿?”
她继续走,目视前方:“我去停尸房。”
“去停尸房干什么?”
“找朋友。”
院长伸手拉她,却发现她的力气奇大!
她一把揪住院长:“你是朋友?”
院长的魂都吓散了,他拼命挣开她的手,闪开几步,大吼道:“你梦游!”
葛桐听了这句话,骤然瘫倒在地……
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对梦游一无所知。
有一天,院长找她聊天,听她讲她过去的故事。院长筛选出了这样一件事:
她读小学的时候,见过一次死人,那时候她在农村,死者是个女性,死者家属为她画了口红,那场面令她无比恐惧,深深烙在她的脑海中……
被院长震醒之后,葛桐不再梦游了。
这就牵扯出一个如何正确面对死亡的问题,属教育范畴,略去。
又一次黄玉凤医生和葛桐值班。天黑后,黄玉凤医生走进葛桐的房子,他第一次笑得这样明朗。他对葛桐说:“葛桐啊,上次我们一起坐车,你不是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现在我告诉你吧。”
黄玉凤医生麻利地打开他的皮包,里面竟然都是美容工具和化妆用品!他抽出一把锋利的剪子,突然不笑了,紧紧盯着葛桐的眼睛说:“我的最大愿望就是给死人美容。”
葛桐吓傻了。
他一步步走近葛桐,他手中的剪子已经逼近了葛桐的喉管:“你给我当模特,好不好?”
|
|
|
本文共收到鲜花 ×0朵;被砸鸡蛋 ×0朵;被砸鸡蛋 ×
2
个 [觉得本文写得还行送朵鲜花,如果不好砸个鸡蛋] ×
2
个 [觉得本文写得还行送朵鲜花,如果不好砸个鸡蛋] |
| 说明:本站部分内容收集于网络,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会第一时间删除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