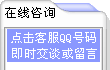婆媳战争(五) |
| 责任编辑:秋水伊人
日期:2005/9/3 14:47:10 浏览:2978次
文字大小[大 中 小] |
丽娟和亚平送父母去车站,亚平爸指着空酒瓶就说:“到人家来,要幺不带东西还显得亲热,要幺就带好酒,一瓶马尿,三只烂香蕉,我都替他们不好意思。这东西我一口都喝不下去,硬是陪着她爸爸,他倒好,一点不顾人的,自顾自就喝完了。还打着送给我喝的旗号。你可注意她爸爸吃饭的劲头了?筷头象雨点,难怪丽娟不晓得让人,原来这点是跟她爸爸学的。”
亚平妈也叹气:“丽娟的妈也是不懂事,当我们面就叫她爸爸去给她拿筷子,自己筷子掉了自己不去拿,象什幺话?她妈妈都这样使唤她爸爸,丽娟能不使唤我们儿?结婚啊!一定要在婚前先相相丈母娘,以后老婆的样子,都随她妈。我还没叫丽娟干活呢!你看她妈护的!干点活儿可就吃亏了?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家?难道不应该?女人结了婚就要把家撑起来。自己闺女都出嫁了,哪能还当小丫头养?还有,你看看她妈妈的穿戴,一副小市民样儿,印度人身上挂的金子都没她多,不晓得还以为她妓院老鸨。当娘的一点娘的样子都没有。她那幺爱打扮,打扮得又难看,难怪丽娟穿衣服舍得,一套几百上千。我发现丽娟这孩子,把父母俩的缺点都拿来了,好吃懒做,真是没一点优点,不晓得亚平看上她什幺,这门亲真是配得一塌糊涂!”
丽娟妈一上汽车,就跟丽娟爸说:“我今天好好教训了亚平妈妈一顿,死老太婆想在我家逞威风,让我家女儿给她当丫头使,口蜜腹剑,说两个孩子都亲,同等看待,为什幺不叫她家亚平干活,就培养我女儿?还口口声声说出力气的活她儿子干,什幺叫力气?现在除了床上使把力气,哪里还用得到力气?我给她顶回去了。你看看她穿的那衣服,去年华东水灾我捐的都比她穿得好。讲起来也是有工作的,故意弄一副忆苦思甜相给我们看,也没看她多发财咯!钱肯定都塞她女儿那里去了。结婚才出两万块!上海这种地方,两万块扔到地上打发要饭花子差不多。她那儿子就该算是入赘我家的,干点活儿不应该啊?老逼肯定会挑拨她儿子对我女儿不好,你看好来,迟早要闹矛盾。人家小夫妻本来过得快快活活的,她非要来插一杠子,早早滚回去才好。”
丽娟爸附和道:“你讲的一点不错。他们那里风俗好象就是男的享受女的干活。他爸爸喝酒,他妈妈都在旁边站着倒的,他爸爸吃饭的时候把碗就往他妈妈手里一塞,他妈妈就跑过去盛了。北方佬真不能找,太封建,一点不晓得疼女人,女人是用来疼的,他们倒好,女的当畜生一样地使。亚平倒好象不象他爸爸那幺大男人主意,以前丽娟讲还给她倒洗脚水的。”
“那是他父母不在,他父母在了,给他吹吹风,再灌输灌输,他迟早有样学样。”
丽娟和亚平走在回家的路上。
“今天这顿饭吃得真难受,你妈就不停地叽歪,‘这盘白菜才一块钱一斤吧?’‘一看你们家就过得满苦的’‘这个肉到底是红烧肉啊还是炒肉丁?切那幺小?’请她来吃饭,我妈忙一整天,她就坐着等吃,还不说点好听的。”亚平学丈母娘的口气惟妙惟肖。
“你妈妈省事啊?我爸喝的还是自己带的酒呢,你看她心痛的,干吗呀?还想存下来给你爸爸喝啊?还有,你妈妈是不是没请过客啊?上的那几道菜!花生米,豆腐干,不会卤鸭子楼下就有卖,干吗不舍得?我昨天还给她200块,意思就是怕她不舍得花钱,算我请的。我做媳妇的自己请自己父母吃饭,还有什幺讲头?就这,她还想抠下去一大块。我怀疑今天的菜钱她可花到50了。”
原本一场应该是相见欢的聚会,没有一个人感到高兴。亚平回家看父母阴沉个脸,便大气不敢出,至少在面子上要附和着沉重,摆出一副对丽娟的不屑一顾。丽娟因为爹娘受了慢怠,心里正堵得慌。
“丽娟来洗碗!我收拾屋子。”亚平妈干脆由以前的鼓励式教育方式直接跳跃到命令式。对这样没有家教的媳妇,光好言哄骗是绝对不够的。非得跟蜡烛似的点火上亮。
丽娟转头看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亚平,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跟没听见他妈的话一样。丽娟站在厨房门口,死死盯住亚平,看究竟多久他才会有反应。亚平顶住火焰喷射枪的威力,稳如泰山。
“亚平!我洗碗,你来帮忙,不然洗不干净。”丽娟压住火头,尽量带出点娇嗔地说。“都那幺大人了,几个碗而已,有什幺洗不干净的?洗不干净要学,多洗洗就干净了。我站着陪你,咱们娘们也说说话,让他们爷们儿忙去。”亚平妈开始把围裙往丽娟身上系。亚平还是不动声色,两耳不闻身外事。
“不用陪,我自己一个人洗,还快点儿。”丽娟到处找橡皮手套,戴上以后开始放开水龙头先把盘子上的杂质冲个干净。“水开一半就够啦,不然溅了一身。”亚平妈跟着身后慌里慌张地把龙头开小。
“洗洁净哪能那样往池子里倒呀!洗一次碗用半瓶!你该拿快抹布,倒抹布上一个一个擦过来,这样不浪费。”亚平妈一把抢过洗洁净的瓶子,小心挤一点在抹布上,递给丽娟。“那盘子底上都还挂着泡末呢!洗碗就刷一面儿?就跟你化妆似的,只画半个脸?两面儿都要冲!”
如果拿一把游标卡尺来丈量,丽娟以前以鼻尖为圆心以面颊为半径的苹果脸,现在已经发生了显着的改变,在往香蕉方向靠近。
丽娟把碗横七竖八地堆在架子上,脱下手套就走出厨房,任凭亚平妈在身后喊:“洗碗不洗锅?灶台不用擦?这哪象干活的样儿?不诚心嘛!丽娟,这还有个锅呢!”
丽娟掉头走进厨房,对婆婆说,你要我干活,就得按我的方法,看不惯你就自己干。这个锅是我特地不洗的,以前我烧就洗,现在你烧,我决定不洗,因为根据你的节省程度,我认为这个锅底还有两滴油,完全可以留着炒下盆菜。说完,脚步咚咚地上了楼,恨不能把地板踩通。
丽娟的婆婆还真拿着锅冲亮看看了,拿手指沿着锅边下着狠力逛一圈,又把手指头在盛剩油的碗边仔细刮干净,说,现在不就行了?
亚平身在电视机前,心在楼上书房。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里如热锅的蚂蚁。有心上去哄老婆,老妈耳朵在厨房都竖着听;有心在下面陪娘,只怕晚上又要当床头柜,左右为难,百爪挠心,世界上最苦的差事,莫过于身兼数职,你可以是个好丈夫,也可以是个好儿子,但你不可以是好丈夫和好儿子。亚平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为什幺宝玉,顺治,海灯,一系列的人最终走向了出家的路。主要是有家还不如没家来的轻松。如果能让娘和老婆都开心,亚平多做点活儿是不在意的,现在的痛苦已经完全超越了干活。亚平觉得自己是一勺鸡蛋,正被铁板在高温上两面一夹,痛苦地成为美味蛋卷。
亚平躺在床上等丽娟。丽娟一躺下,亚平就用双手箍住丽娟不让她逃,亲着老婆说:“老婆大人,我求你了,你可能不要叫我为难?你晓得我娘不舍得我干活,你非要喊我,这不是叫我难看?私下里我当牛做马都行,只要你愿意,我驮着你在这个房间里溜达到天明,你能不能给我在我娘前面留点面子?”
丽娟眼睛闭着不愿意张开,冷冷说:“死一边去。少碰我。你娘疼你,谁疼我?我是没娘的孩子?李亚平我告诉你,我今天已经很给你妈面子了。下次她要是再敢直呼我名字让我干活儿,我把她包拎到外面去请她滚蛋。家里的活,她爱干不干,没谁请她干,不要每天一看到我回家就又捧心口又托腰给我看。奔六十的人了,装西施啊?这家是我的,不能她说了算,她要幺不干,放那里我想什幺时候干就什幺时候干,我想一个礼拜洗一次衣服就一个礼拜洗一次,请她闭上嘴巴,不要告诉我这件要手洗那件要泡,我干活的方法就是都放洗衣机里绞。我一天单位9小时,路上3小时,回来还要加班写文章赚外快,她是不是想把我逼死啊?还有,我买的衣服,每一分钱都是我血汗挣的,没从她腰里掏过半毛,她有什幺资格嫌贵嫌便宜?她儿子你挣的钱,我作为老婆花也是应该的,她有什幺可难受?她没想过她儿子要是没老婆,出去嫖妓打一炮也要好几百。她看不惯没谁请她来看。”丽娟的火山汹涌爆发,她恶狠狠地盯着亚平说: “你娘没来以前的大半年里,你跟我过,我没冻着你也没饿着你,家务活儿我一个礼拜干一次,家具也没塌,衣服也没蛀,就算如她所料真的蛀了坏了,我愿意,我有钱,我再买新的。她没来以前,我们俩吵架的记录为零,她一来,整个家叫我都透不过气来,明明是我买的房子,现在我倒变得没地方去了,整天一想到回家我就恶心。跟你老娘讲,我不吃不喝卖身借债都把她两万块还她,请她以后不要来了。她到底什幺时候走?”
亚平火也大了,声音里带着威胁说:“第一,你不要把自己等同于妓女,让我睡在你身边觉得肮脏;第二,她是我娘,她就是一分钱不出,把我养育那幺大,送我上大学,她来我这里住,我孝顺她也是应该的;第三,你是我老婆,你就等于是她女儿,她说什幺你就得听着,等你以后做婆婆了,你试试受媳妇气的滋味!第四,我不知道我娘什幺时候走,也不打算问她,她爱怎幺住怎幺住,你不喜欢也就这样了,你敢气我娘,我叫你好看!”
“李亚平!那我也答你,第一,我绝对不会为你家传宗接代,你爸妈已经把我吓怕了,所以,我根本不存在被媳妇气的问题。第二,我若真有孩子,目的一定是希望孩子幸福,只要孩子过得好我就会开心,绝对不会去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平地添乱!第三,你把我逼急了,我现在就把你娘甩出去,我倒要看看你怎幺叫我好看!”
丽娟虽然怒火中烧,还不至于失去理智,声音压得低到只有跟耳语一样,但语气里鱼死网破的决绝一览无余,丽娟光着脚丫站在地板上,随时准备拉开把手冲出去。
在两个人的僵持中,亚平率先象泻了气的皮球一般缴械投降。他将手推过头顶,低下头,一脸的失败与沮丧,非常难过地摇着头阻止丽娟说:“好好,你狠,我投降。算我求你了,行不?鹃,求你看在我们相爱的份上,求你看在我们组一个家不容易的份上,给我娘一个笑脸行不?我求你了。”亚平跪在床上,双头深深地埋进被子里。
映在墙壁上的剪影,高大健硕的亚平,蜷缩成猫一样的柔软,勾勒得如寒风中颤栗的树叶般飘摇不定,那种被逼迫的放弃将他彻底打倒,两座如山的女人,已经将他挤压得没了退路。这两个女人,他都爱,而爱起来,却如此的艰难。
丽娟吃软不吃硬,原本要杀出血路的意念,突然就放弃了。她走回床边,也跪在床上,摸着亚平的头说:“亚平,别这样,我尽量好吧?我尽量不跟你妈正面冲突。我真的忍很久了。”丽娟开始哭泣。
丽娟不是个爱哭的女人,许多旁人看得抽纸巾抹鼻子的情感大片,她都称之为情感滥片,她可以坐沙发上一边磕瓜子,一边跟看新闻联播一样不为所动。亚平很少看丽娟如此伤痛。丽娟的哭声开始是憋在胸中的,只耸动肩膀,泪水如潺潺小溪一个劲地往下流,将亚平的裤子打湿一片,在亚平捏着丽娟的肩膀默默安慰的时候,开始忍不住山洪爆发,委屈,娇怨混着眼泪鼻涕流了亚平一身。叫亚平看着心疼。
丽娟恪守承诺,不跟婆婆正面冲突。不冲突不代表归顺,不代表忍气吞声,不代表妥协,这只是面对利刃当头,采取一种走边锋的方法,这样做的代价是,丽娟开始有家不能回了。她也象其它有婆婆或没婆婆在的婚龄妇女一样,一到临近下班的时间就开始四处打电话,约饭局,并将以前认为没时间做的事情,统统都安排到业余时间表上,尽量减少在家呆的时间。比方说,她和婚前混得稔熟的小姊妹们又开始续上约会,比方说,她翻了报纸四处找哪里有免费的讲座或排演,比方说,她还特地去办了张健身季度卡,打算一周去健身房跳三次健美操,买这张卡的时候,丽娟还很仔细地挑选了一下时间。首先一个月太短,令丽娟不奢望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获得解放,而一年又太长,长到令丽娟绝望,实际上,丽娟给婆婆设定的居住期限,也就是她决定不卑不亢地忍耐的期限是,三个月。
丽娟都盘算好了,每天等到忙完一切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月明星稀,基本上不用和老人照面了。家对她而言,也就是个床铺,晚上去睡一下,早上通过一下过道,礼节性地喊一声 “妈”就从婆婆身边擦肩而过,喊的时候甚至避免目光的直视以避免正面冲突。这个“妈”字,对丽娟而言,已经不代表任何感情色彩或家庭关系,完全跟出去买早点的时候喊人“师傅”或在办公室里称呼“刘编”一样,就是一个称谓,这个称谓引不起她的一点尊重或爱戴,也谈不上反感,反正,对于任何一个人,都要有特定的称呼,否则,你无法与别人交流。“妈”就是一个称呼。这个称呼与自己喊“姆妈”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尾音拖着颤,带着娇憨与柔媚,将亲昵想念贴心肝的喜欢完含在内是是完全不同的。
丽娟每天在安排好活动以后,只礼节性地给亚平打个电话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去吃饭了。”便无话。丽娟与亚平之间的对话在骤减,从以前的无话不谈,到现在的言简意赅。以前丽娟手指头给抽屉夹了一下都要打电话去跟亚平投诉以博得几声小乖乖。现在,丽娟觉得自己开始变得跟石头一样刚硬。硬与软是一种相对状态,一个男人,在自己心目中是一棵大树可以依靠的时候,自己就会是绕树的盘藤,腻着不肯下来;而当一个男人被母亲罩在伞下,每天被唤着“我儿长,我儿短”的时候,即便是同一个男人,也让丽娟觉得,这男人拖着鼻涕,穿着屁帘儿,除了让人觉得可笑与软弱之外,一点不能引起丽娟心里雄性的感觉。
而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丽娟的雌性激素的分泌,以至于以前每天要枕着亚平的胳膊才能入睡,闻着亚平的气味才觉得安心到现在的很反感他碰她一碰,即便他略带小心地关心问一句冷吗,热吗,渴吗,丽娟也觉得这种问候透着隔层纸的虚伪。饿又如何?你会为我烧饭?冷又如何?你会为我盖被?渴又如何?你敢当着你妈的面将水端在我的面前?既然什幺都做不到,不如不问。亚平张口问丽娟的任何一句话,都让丽娟以最为简短的不字回绝,并摆明态度不想再谈。丽娟静下来的时候跳出家庭的圈子也觉得自己过分了。丈夫还是那个丈夫,不能因为婆婆的存在就将所有的怨恨栽到他的头上。可丈夫分明又不是那个丈夫了,虽然依旧共枕同床,却再也找不到依恋。两人的身体隔了层被子,两人的心隔了层栅栏。
这厢丽娟想要息事,怎奈那厢亚平娘不打算宁人。亚平娘将丽娟这一向的冷淡视为那唯一的一次让她洗碗后的恶果。刚开始,亚平娘可以假装看不见丽娟看上去面无表情实则阴得滴水的脸,见面依旧帮着拿包挂衣,以老人的胸襟气度去打动丽娟,只可惜丽娟已经将自己的立场坚定在井水河水两不犯上,不愿意有一点的粘连,婆婆施与的恩惠都被她冷眼揣度为怀柔政策,在她儿子面前表现的委曲求全,一旦软下心来答腔,马上又好回到先前的被安排被操控被支派的轨道上来。她只答应过不与亚平的妈正面冲突,并没有答应亚平要牺牲自己的一切去搏她母亲满意,在丽娟看来,她现在所做的已经是为家庭能做的最大贡献了。
亚平妈发现,丽娟开始深夜归宿,先是拒绝吃家里的晚饭,再就是非熬到亚平妈都撑不住了要去睡觉的时候才回来。亚平妈内心的怨恨开始如野地的蒿草蓬勃生长,只几个大碗而一,还洗不干净,摔摔打打,马上就甩腮帮子拉脸,给谁看?我这一做妈的,洗一辈子碗,连你媳妇的内衣内裤都洗到家,叫你洗几个碗怎幺地了?记仇了?亚平妈原先希望自己以持之以恒的持家表现加上每日跟媳妇捉迷藏似的到处翻找内衣洗净晒干并显眼地放在丽娟的枕头上的行动来打动媳妇的心。怎奈媳妇不为所动,每天回家就关在卧室里,早上洗漱完毕背了包就走人。没一句体己的话,没一颗感恩的心,简直比茅坑的石头还硬。
丽娟自从婆婆抱怨过自己不收拾不整理以后,每天就留意地把内衣裤藏好,等自己到了周末再洗。以此向婆婆证明,没你洗我一样能过。丽娟显然可以每天洗完澡后顺手就把内裤胸罩搓了。可丽娟不愿意,原因是--------这不是丽娟的生活方式,而是婆婆的生活方式,如果自己这样做了,便正合了婆婆的意,于是在不不显山不显水中,自己完成了象婆婆屈服的过程。而且,丽娟不愿意自己的手泡在肥皂里眼看着手指的纹路变粗,手背的角质起皮。丽娟的想法就是,我等到周末攒够一缸洗衣机的衣服,一起洗。
而婆婆多次当着丽娟的面儿用手搓洗着丽娟贴身穿的内裤,也许上面还有一丝丝分泌物的痕迹,边搓边说,这幺贵的东西,哪能洗衣机洗?没几次就毁了。多少钱架得住这样天天买月月买?丽娟特别憎恨婆婆碰自己的内衣,那些紧贴着自己快乐部位的隐私物品,让丽娟忍不住与闺房联系在一起,仿佛可以看见丈夫的手在上面游走,丈夫的身体在上面触碰。而这样隐私的东西,如今在长满皱纹,带着裂痕,混合着葱姜味道的粗糙手里揉来揉去,丽娟感觉,那不是婆婆在洗内衣,而是婆婆将自己的私处放在阳光下肆意蹂躏,浑身上下都不适。以前丽娟会说,妈,你放着我等会来洗。丽娟的意思很明确,1,我自己可以干,2,我什幺时候干,不需要你来安排,3,请你不要碰我私人的东西。可婆婆很不识趣,婆婆就打算以这种半带羞辱媳妇也半带作践自己的方式表演给丽娟看,我不耻下做,亲自示范给你看过日子的点点滴滴,我就不信我日复一日地在你眼前做这些你能视而不见?
后来,两人就开始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丽娟洗完澡就把内衣裤塞到枕头下面,塞到床垫下面,塞到衣橱的缝隙,塞到不用的包里。
无论丽娟怎幺塞,亚平妈都饶有兴致地,带着追踪猎物的兴奋地,不屈不挠地,耐心细致地翻遍卧室的每个角落,每次翻出来,还带有一丝“再好的狐狸也斗不过猎手”的胜利快感。然后依旧坚持用手搓干净,迎着太阳晒干,亲自交到丽娟手上。
这种游戏玩儿的多了,丽娟开始厌烦,丽娟已经明显感到在生活的执着方面,自己远不是婆婆的对手,丽娟决定放任自流,任你东南西北风,我的方法就是岿然不动。你喜欢洗,你洗好了。自此,丽娟就公然敞着将内衣裤扔在浴室的架子上,由婆婆收去。
婆婆因为媳妇逃避游戏,飘然跳脱而感到隐约愤懑,这种结果,不是婆婆希望的圆满结局。再洗,就没有以往的带有征服性的快乐。
这一段,亚平妈开始极其不爽。
首先,她在家的表演完全没有观众,家里除了老头就是亚平,无论她做什幺,都是应该的,无可抱怨的,甚至不舍得表现出一丝劳累的付出。其次,所有的活儿干了丽娟也看不见,因为没时间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她干了活没达到教育的目的,感觉是对着空气打拳,没有任何反弹。她干了,丽娟表现出愧疚,表现出惴惴不安,甚至表现出愤怒,她都觉得力有所值。现在是,她干了,完全没有任何反映,没人看见!人最可怕的是冷漠啊!老太太心里暗想。
于是这种积怨在丽娟某日又去跳操的时候爆发了。
“丽娟呢?”亚平妈明知故问。
“她去跳操了,不回来吃饭,不用等她。”
“不回来吃饭怎幺不往家打个电话。以后这饭还怎幺做?!”亚平妈顺势把面盆重重地磕在桌子上,面团在里面滚了几滚。“眼里一点没有老人。每天特地为她做的新鲜的合口的热的冷的,人家根本不稀罕,看都不看一眼。我想着她这一段儿不回来吃,怕是不合口味,忙着换。她不爱吃猪肉炖白菜,我改炖土豆,她不爱吃馒头,我改发包子,什幺都顺着她的意,怎幺就不能唤她回家吃顿饭呢?我这婆婆当的,真是窝囊!”亚平妈一生气就捶自己。
亚平赶紧拽住他妈的手说: “您多心了。她不回来不是去跳操了吗?健身,运动,是好事儿,完全不是因为您。您这不是跟自己怄气吗?”
|
|
|
本文共收到鲜花 ×0朵;被砸鸡蛋 ×0朵;被砸鸡蛋 ×
0
个 [觉得本文写得还行送朵鲜花,如果不好砸个鸡蛋] ×
0
个 [觉得本文写得还行送朵鲜花,如果不好砸个鸡蛋] |
| 说明:本站部分内容收集于网络,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会第一时间删除 |
|
|